锦州来客
1969年,川仪总厂受到冲击。
许传江和他在辽宁晶体管厂(以下简称“辽晶”)的同事,穿过一片写满了标语的报纸,绕过几群大声叫嚣的年轻人,从成字128部队基建工程兵的一声叹息中穿行而过,来到川仪六厂报道。
许传江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简称“川大”)半导体专业。刚入学的时候,他就读于川大核物理专业。
但1962年秋天,在川大因饥饿盛行甲肝的时节,他在校门口突然昏厥。休息了一年时间,他的父亲认定此事和苏联援建的反应堆不无关系,于是命他转到另外一个王牌保密专业——半导体。
半导体是一个香饽饽专业,许传江的上一届学长都分配到了大城市的紧要机关单位。
有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也有去上海元件五厂的,这两个单位一有大城市户口,二是全国实力最强,经费和待遇是不用提的。
对于一些鞋都穿不起、赤脚来上学的川北山区同学来说,大城市的半导体单位无疑是一个“鲤鱼跃龙门”的纯金饭碗。
但许传江这一届的运气实在不好。
1964年的全国人才计划会上,川大半导体大部分到了辽宁。很多学生分到了专业不对口的无线电工厂,非常不满,学校得知向高等教育部打报告,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相比之下,许传江要幸运一些,但也不能说幸运多少。
许传江倒是专业对口,分配到了锦州的辽宁晶体管厂(简称辽晶)。学校一宣布分配单位,他立马带着报到证,卷起铺盖,也不回成都老家,直接买了一张到沈阳的硬座。
辗转来到锦州,他发现,辽晶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研究所,在辽宁省内却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不到一年时间,他因工作优异,迅速升为实验室主任。
但是,许传江不久便遭了殃。动荡时期,辽晶停工,几十位大学生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许传江也不例外。
绝望之际,正在建设半导体工厂的机械工业部向电子工业部要人未果,最终找到了不起眼的辽晶。
经过一番运作,机械工业部把包括许传江在内的47个经验丰富的半导体人才捞了出来,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仪六厂。
许传江多少感到一些幸运。
最为动荡的两年已经过去,中央下达了促生产的指令,军管会实际上全面接手了全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重庆“815”和“反到底”两派的激烈斗争如云烟般消散,生产秩序渐为好转。
技术骨干虽然并不掌握权力,也惹不起别人,但起码可以开展业务。
一天,厂长杨继元把许传江叫到办公室。杨继元在建国后跟随部队南下,原是川仪总厂供应处的负责人,后转到六厂担任厂长。他对许传江说到:
传江,虽然你顶着工艺组组长的职务,但实际上是总工的角色了,要大胆的工作!
打开局面
在川仪总厂数十个分厂中,川仪六厂是个异类:虽说由机械工业部决策成立,但做的是电子工业部的产品业务。
机械工业部不熟悉半导体,为川仪六厂规划的半导体产能,数倍于总厂需求。脑门一拍多出来的产能,对于六厂是一个不小的灾难:
产能无法在机械工业部包销,半导体需求大户——电子工业部,又不是自己的领导。
就这样,川仪六厂成了一个没爹疼没娘养的孩子,要想生存下去,只能出去要饭吃。
以许传江为代表的“辽晶集团”的加入,为川仪六厂输入了新鲜血液。
厂长制订了工程师即销售的策略,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打开销路。许传江奔波于各种电话会、计划会和订货会,遇到电子工业部的电子厂,马上扑上去,为他们展示、讲解六厂的产品目录。
全国订货会是最重要、也最高效的销售场合。
机械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轮流在各大城市开会,会议的承办方——一般是当地的国营工厂,会租下一个学校的大礼堂,摆上数百张课桌,上面横放着来自全国厂商的样品。
川仪六厂的工程师坐在桌后,需求方在会场上走来走去,相中了便与他们商谈。双方议定产品卖价和交期,当即签订合同,分别交由在场的两部委盖章,几天下来,几乎大半供需可以敲定,速度极快。
在一个半导体极为紧缺的卖方市场,国营工厂几乎不用愁销路,这让很多厂商养成了“坐商”的习惯,等着客户来上门。
但川仪六厂毕竟不是电子工业部体系内的,对需求还是远了些,工程师也就需要多出差,以弥补市场信息上的不足。
1971年,许传江带着本厂的两位年轻工程师经由川黔铁路到达贵阳。一下车,他们直奔贵州省机械厅,对方仔细翻看产品目录,和贵州省内各厂汇总上来的需求一一对照,以决定到底订什么货。
只拿着一本产品目录是远远不够的,出去推销产品,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多兵种作战。
同样位于重庆的716厂是川仪六厂的大客户。
许传江每次拜访,必带上一位做工艺的同事、一位懂电子线路的同事。判断到底能否接单,首先要当场研究好无线电工厂设计的线路方案,确定能做了,然后是工艺质量的问题。
工艺和线路双管齐下,川仪六厂的工程师白天推销,晚上研发,很快解决了销路的问题。
军工名厂
随着“辽晶集团”在北碚生根,川仪六厂迅速培养起了自己的技术能力。
东方红卫星上天,需要一个存储器把《东方红》这首歌和遥控遥测信号存起来,难度颇大,进口不到。
负责该项研究的成都电子科大(以下简称“成电”)教授走访了许多军工企业,对电路质量都不甚满意,幸而最终在川仪六厂——一个几乎没怎么听过名字的边缘企业找到了中意之物。他
说到:
我们就不管你们是哪个部的了,只要你有好东西,我们就买。
机械工业部脸上有光,事后主动拨来三个研发基金予以支持。
川仪六厂一炮打响,他们制作高质量半导体产品的能力在军工航天体系传播开来。
中国的高炮部队赴越南参战,从战场上捡回通讯机、雷达辅助瞄准装置等美军电子设备,如获至宝。就着美军送来的装备,川仪六厂的工程师耐心学习,最终制造出高质量的成品。
之后,负责洲际导弹的七机部也与川仪六厂建立了合作关系。有次实在着急,七机部部长跑到重庆,住在市委招待所秘密等待生产进展的消息。
因为导弹要上天,如用电子管自动控制,便是成百上千只笨重的累赘塞到里面,既占面积,电力消耗又快,数据传输慢的像蜗牛。只有较高集成度的门电路和线性电路,才能满足导弹升级的需求。
完成七机部的紧急任务,许传江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会讨论。
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发射厂、塔台控制室和液氮站,也第一次知道,自己生产出来的半导体,与国家的武力和命运紧密关联。
不过,此时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本的财团法人正在急切推进半导体在消费电子等民用市场的应用,他们沉潜已久,在国际市场上四面出击,对美国半导体王座的挑战之势日渐彰显。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迎来了一次罕见的发展机遇。
飞来的机缘
1984年初,川仪六厂的工程师们茶余饭后,经常兴致勃勃的纵论全球大势,谈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半导体产业。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中国幸亏没有步苏联的后尘。苏联的第一台计算机装了2000个真空电子管,足足有两栋大楼那么大,从那之后,苏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彻底偏离了电子工业的主流技术方向——半导体。
虽说中国走对了路,可川仪六厂快二十年,也就只能生产些二极管、三极管,还有容量1kb的存储器,和集成了几百个晶体管的芯片。这些半导体结构简单,远远比不上美国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试想一下,他们竟然能往半个指甲盖大的地方塞进去三万个晶体管,这还了得!
大家垂头叹气,抿一口茶。一位老练的工程师突然说到:
谁曾想呢,美国人千算万算,自作聪明,竟然把机密泄漏了出来噻!
说到这个地方,那人突然停顿了一下,瞬间勾起了办公室所有人的兴致:
那美国总统唐纳德·里根是个演员,给国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竟然公开讲到,只要我们计算机和芯片技术对中国保密的好,是叫保密,不叫封锁,那么,我们就不怕中国强大。
这句话让我们高层听到了,感到很吃惊,最后就下决心要搞上去,用外汇去买旧的生产设备,也是很好的。
众人皆以为然。无锡742厂的日本引进项目正如火如荼,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芯片热。中央原来八个工业部门,每个都有对应的终端机械产品,也有权限向国家计委申请配套的芯片项目。
可是,川仪六厂似乎是没人疼没人管了。六厂只能卖一两块钱一块的半导体,暂时还不能卖其他大厂那样十几二十元一套的高价芯片,只能等别人做了出来,再拿来仿制、出售。
六厂的机会
没有引进项目,不单单是六厂的工程师们焦心,总厂厂长孙同川也在到处留意。
孙同川,北方人士,出身工农,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颇为少见的分配到了不对口的川仪。1978年,总厂觉得六厂以北方人士和知识分子为主,一群书生互相不对付,需要一个带头人做好团结工作。
而孙同川,恰好是那个正确的选择。他表情很好,开会说一句话便笑一下,做事面面俱到,众人都觉得可亲可爱。
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央迅速提拔年轻干部。孙同川离开六厂后,很快做到了总厂厂长的位置,与他搭班的是另一位六厂的老同事。由此,总厂对于六厂,也就格外关照。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同川察觉到川仪六厂的潜在机会。
有次与美国的商业贸易团谈判,对方席间提到,美国最近流行“大炼芯片”,菲尼克斯有个房地产财团找了干练的人马,整来成套的设备,最后烂尾了,正在找人接盘。孙同川忙将这个消息告诉外经贸部和六厂的老同事。
不日,陈惠荣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办理此事,批复极快。六厂人人诧异,涉及美元外汇额度,进展一般较慢。
原来,此次川仪六厂引进,有部里暗中协调撑腰。在电子工业部主导芯片项目引进的背景下,还憋在荒山野岭的川仪六厂如能搞定美国人都搞不定的事情,自然要记上大功一件。
1984年,国家计委向川仪六厂下达任务书:
投资3000万人民币,从美国引进3微米CMOS芯片工艺产线。
接下中央下达的任务书,便是纳了白纸黑字的投名状。川仪六厂委任总工许传江为技术组长。他带领一行37个工程师来到北京,在机械工业部位于海淀区的甘家口招待所住下,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学习培训。
培训有一大半的内容是外事原则。一个司长过来培训,讲了“三不”原则:不上街、不私下与美国人交流、尤其,不准叛逃。大家的心情顿时紧张了起来。
考虑到美国总统说过,“集成电路产业的健康与活力关系美国的未来竞争力”,并且,中国的领导层已经知道了美方对中方在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产业上的保密态度。
因而,部里的领导对许传江和他的同事格外强调,严格按照合同行事,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那条二手产线买回来,如果犯规,很容易在美国被抓了。
为了确保这支赴美学习的队伍不出问题,部里派来一位领导负责出国事宜。
在一种略带紧张却抑制不住亢奋的心情下,川仪六厂的中国工程师开始了美国之旅。
省外汇
川仪六厂的引进项目,座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因天气炎热,印第安土著将菲尼克斯称为“凤凰城”,意为“炎热之地”。
当地最大的财团拥有一个芯片工厂,但因经营不善破产。机械工业部的引进项目,正是从凤凰城这家破产工厂接手旧设备。不同于当时众多只买设备却连“使用说明书”都没有的项目,菲尼克斯财团答应教会中方团队使用设备制造芯片。
对于早已擦拳磨掌、却一直没有学习机会的川仪六厂来说,这是一个技术跃进的好机会。
许传江和36位工程师在郊外的汽车旅馆住了下来,发现出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一到美国,领导先把美元都收了上来,国家已为这个项目花了不少外汇,部里当然更要省着用这一点额度。
原本,每个人一天的住宿经费有32美元,吃饭经费有22美元,还有交通费、办公费。现在,一个人统共16美元。工程师们两两住在一块,每天上午和晚上吃方便面和面包,中午得享口福,去一家华人餐厅,只用花4美元就可以吃到一顿有鸡肉的自助餐。
许传江在美国
美国之行时间格外紧张,只有三个月,因此工程师周末也待在旅馆加班。这时,他们有了一天额外几美元的额度,可以再好好吃一顿。
但初出国门的工程师惦记着家里,硬是把本来就不多的美元省了下来,好回国后为家里添置当时最为重要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
省钱,尤其是省外汇,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一个美元的外汇额度积少成多,便可以汇聚成一大笔钱,买下一台珍贵的设备。
但凤凰城郊外糟糕的治安秩序,似乎跟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有时候在旅馆经费上,也不能那么省。
一个周末,许传江加完班,叫上组里的年轻人和翻译去买方便面。几人出了旅馆,走过一条马路,穿过近郊零零星星的住户,走了好一会儿终于到了超市。
买完方便面天已经黑了,几人正走着,一辆货车往路中间一横,几个黑人青年下了车,冲上来大声叫嚷,看着咬牙切齿,是要动手动脚。
许传江望着翻译,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见翻译也是汗流浃背。
双方僵持许久,翻译终于缓过神来,跟许传江讲到,这些黑人说我们是日本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要和我们打架。许传江顿时松了一口气,我们是中国人啊。翻译跟这几个生猛的黑人青年解释了一番,他们马上换了脸色,过来握手言和。
回到旅馆,众人把心放了下来,各自忙碌。到了晚上,一个美国老头又闯进一位工程师的屋里,看起来是喝多了,满脸通红,躺在床上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什么。
川仪的工程师都接受过俄语的训练,却唯独没有学习过英语。一个陌生老头莫名其妙的出现,不能不让人感到紧张。那位工程师不敢去找领导,便跑去许传江屋里汇报此事。许传江急忙放下手头工作,叫上翻译了解情况。
交流了一段时间,翻译对大家说,这个老头是从旁边的州过来的,追踪观察我们好久了,知道我们是友好的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他躺在床上,就是口渴,想跟我们要一瓶可乐。众人大笑起来,原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验收离子注入机
由于中方要在三个月内按照出厂标准验收两百多台设备,工作节奏变得异常紧张,许传江每日忙着做实验,遇到问题向美方工程师请教,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但语言不通还是会为接收工作带来一些问题。
许传江(左四)在凤凰城工厂前与美方人员合影
在所有的设备里,最重要的一台,不是现在人们最为看重的光刻机,而是离子注入机。
在3微米工艺的时代,对于光刻的要求还没那么高,最影响芯片生产良率的,是离子注入的过程。在完成光刻和刻蚀的步骤后,工程师操作离子注入机,70万伏的电压在超高真空环境中以光速运动,把磷、硼等离子精准地纹在硅片的身上。
这一过程可以大致理解为,一个内力极强的人,远隔千米,却能在宇宙中发功,丝毫不差地给人身上的几个穴位来一个葵花点穴手。
离子注入机究竟能否打入,是否打入了足数的离子,离子打的有多深…只有这一系列数据达到标准,离子注入机才算达到出厂标准。
验收之初,许传江注意到离子注入机有个关键的电气指标没有达到,与美方工程师交涉。
对方认为许传江不懂英语难以拿出证据,说到:你们就是不懂。许传江左思右想,回怼不是,马马虎虎通过验收更是难辞其咎,于是带了一位翻译和一位电气工程师,前往菲尼克斯图书馆搜索英文资料,以证我方之明。
为了避免与美国人接触,三人在图书馆找了一张空空的大桌子坐下,面前堆几十本书遮挡正脸,一般不易察觉。
查了半天资料,许传江不经意一瞥,发现一个看着三十多岁的白人女性坐在他正对面,属实吓了一跳,顿时不知所措,僵坐在座位上。
看的资料越多,心里越犯嘀咕。打量片刻,只见那个美国女人身着风衣,身材高大,不断从书架上拿书,引人为之侧目。正犹豫间,她对着三人说起了英语,听起来十分友好,许传江眼神略有迟疑,向翻译点了点头。翻译边听边讲:
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我去过北京和杭州。
话说着,她脱下风衣,里面的T恤上写着一行汉字:我到过长城。她指着那几个汉字,笑了起来。她继续讲,翻译接着说,两位中国工程师听的入了迷:
我是个律师,现在查资料。我的爱人非常好客,你们远道而来,想必有困难。
说着,她拿出一张纸,稍作片刻,把纸片递给许传江,讲到:
这是我的名字和电话,如有任何困难,欢迎到我家里来。
查完资料,天色已暗,图书馆远离驻地,三人决定这次不坐公交,改打的。
走到出租车招停牌前,翻译进入电话亭拿起投币电话机,电话那边传来声音:你有什么要求请讲,翻译说了所在位置和目的地,电话又重复问了一遍,翻译又答了一遍。
打了半个小时,不见出租车的踪影,许传江耐不住性子,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了头:
电话那边那个声音老是问我。
一个投币电话机难倒三个英雄好汉。当时中国鲜有这个新鲜的玩意,许传江一行人在北京也无暇外出,也不知道投币电话机得投币,一下子到了异国他乡,十分焦虑。
就在此时,一个白人老头走了过来。他在附近观察许久,过来问到:我看你们是中国人,你们的人民友善有礼,你们遇到困难,但讲无妨。
翻译回到:我们查了资料不知道怎么回去。那人乐了:我有车!三人还是紧张,商量了一阵,三个人可以相互作证,消除了刻意与美国人接触的嫌疑,于是上了车。一路上,老白人说:
我是德克萨斯州的商人,来这里看一笔生意,你们今天要出去玩么?
三人在后面坐着,尴尬地笑了,哪里敢出去玩呢。老白人把名片和他旅店的电话给了翻译,十分笃定地说到:
你们绝对要有困难的!毕竟在这不熟悉,遇到困难打电话给我,我来给你们看看。
赢得尊重
许传江拿着从图书馆借来的资料,赢得了与美方工程师的辩论,对方不再多说什么,直接找来设备厂维修。
在工厂里,美方工程师开始喜欢这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要接收的设备参数丝毫不让,做起实验来从不马虎,格外较真,讲起笑话来他们总是笑呵呵的,却笑而不语。
中央情报局曾几次来工厂警告两方不要交流工艺文件等工业机密,但并没有阻止双方私下往来。美方工程师盛情邀请中国人周末去家里做客,他们却总是说周末要开会。
在所有的美国工程师里,一个印第安人工程师对中国人是最为友好的,他甚至把经常一起工作的许传江当成了诉说知心话的朋友。
许传江在旅馆旁
在许传江看来,印第安人技术一流,完全可以当一个“总工”。
任何设备出了问题,他却总是言辞谦卑地给白人善后。他受益于里根总统的自由化新政,收入翻了一倍,娶了一个漂亮的白人老婆,在工厂里却是一个兼职的服务员,端茶倒水迎来往送都是他干,甚至中方参与菲尼克斯财团的鸡尾酒会,也是他的弟弟开车接送。
作为凤凰城历史最为悠久的土著居民的后裔,这个印第安人自认为没有“政治地位”。
从印第安人的口中,许传江了解到为什么这些天遇到的美国人对自己这么好:不仅仅是芯片,美国的汽车业也正在面临日本车的冲击,工程师们在失业。工厂上下没有人不对日本政府咬牙切齿,工厂每况愈下,裁掉的白人渐多,全是日本人搞的鬼。但是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
经过三个月的忙碌,验收即将完毕,中方总算可以松一口气。菲尼克斯财团的大老板邀请中方工程师观看周末的全美橄榄球决赛,领导难得松了口。
工程师们乘着一辆大巴来到体育馆,立马被馆内的场景震撼到了。
全美橄榄球赛是这个国家最为鼎盛的赛事,观众的欢呼声直上云霄,直升飞机上挂着长长的横幅,在天上飞来飞去,一些挂着工牌的记者坐在飞机上,似乎在激动地解说着这场比赛。
因是临时加塞,大老板给赛事组织方打了个电话,在走廊加了几十个座位。工程师们坐定,看到一群人抱着橄榄球到处跑。虽是看不懂,仍然被前面高声呼喊的美国人点燃了情绪,非常兴奋。
飞机上的一些记者眼尖地注意到,赛场多出一排略显沉默的中国人。美国记者明显迅速抓住了赛事间隙最大的卖点。于是,飞机的LED屏幕上打出来一行英文: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观看全美橄榄球联赛!
一时间,全场的美国人起立,朝着坐在后排的中国人鼓掌。掌声响彻体育馆,这场赛事因为中国人的到来达到高潮。
全美橄榄球比赛为川仪六厂的赴美引进之旅做了一个漂亮的总结陈辞。许传江却没料到,设备即将启程回国的时候,将有一场不小的灾难。




















 1905
19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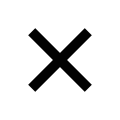
 下载ECAD模型
下载ECAD模型

.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128,h_96)
.jp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w_128,h_96)



